
吴烨彬在华坚集团非洲的工厂里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杨 海
35岁的吴烨彬见证过华强北的潮起潮落。
这个从华强北柜台起步的资深创客创立过3家公司,注册过4个品牌,开发出的样品堆满一间36平方米的仓库。其中一些带来财富,一些带来教训。
当年的华强北模式如今沉没在时代的水底,吴烨彬奋力游出水面,继续追赶潮头。
他最新的产品已经众筹了298万美元,进入最后的测试阶段。下个月,他将出现在非洲,把获得版权许可的电影、歌曲卖给当地人。当年大学毕业后,吴烨彬在华强北卖光盘,内容是当年在深圳“比周杰伦还要流行”的余世维企业管理课。
一部短片以他为拍摄对象,记下他的过往:2010年,大学毕业不到3年的吴烨彬,靠华强北的电子产业发家。
那是华强北最繁荣的时代,一米柜台后走出亿万富豪的故事不断上演。他们开发的产品遍布全国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手机柜台,以夸张的外观或功能为卖点,设计者可以自由挥洒创意。
但这里原始的贸易形态,终究经不起互联网时代一批行业新贵的全面碾轧。3G全面铺开后,依靠运营商的补贴和已经培育起来的供应链,一些国产品牌快速崛起。他们带着全新的商业模式,把华强北数不清的小厂绞杀殆尽。当年打着“时尚”标签的小厂功能手机,现在以另外一种名字被人熟知:老人机。
如今的华强北,各大品牌的巨幅广告覆盖在大楼的外墙上,曾经的临街小门面商铺,已经被品牌专卖店占据。
吴烨彬的办公室也从华强北搬到了深圳湾科技生态园,与商汤科技、欧菲光等中国明星科技企业为邻。其中一些企业,技术已经领先全球,成为华为、苹果和三星的供应商。它们都是潮水退却后,成功上岸的精心耕耘者。与众多流传于世的商业传奇不同,这些企业的转型没有太多波澜壮阔的故事——在深圳,没有什么能够长期保持静止,改变总会自然而然地发生。
无数草根像当年的吴烨彬一样,从全国甚至全球各地涌向深圳,期待在这里获得成功。如今,他们的命题叫作创新,他们渴望依托的,是这里基础深厚、根须发达的电子产业链。
而吴烨彬的下一站是非洲。他把自己的精力分配在深圳和非洲之间。事实上,他在深圳湾科技生态园办公室楼下的邻居,就是一家在非洲大名鼎鼎的“独角兽”企业传音控股。这家成立于2006年的手机企业,如今在非洲市场占有率接近50%,它的产品号称“非洲机王”。
1
吴烨彬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,那时天还没亮,冰凉的空气灌进鼻孔,周围安静得只有鸟鸣声。但他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涌动,他说那种感觉就像当初在华强北时一样,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肾上腺素驱使他向前冲。
吴烨彬对华强北最深刻的记忆,是每天傍晚,市场里此起彼伏的撕扯胶带的声音。
一天的生意结束前,商家们把手机、平板电脑和一些叫不出牌子的上网本打包封箱。快递工人把它们堆满拖车,吆喝着穿过人群。通过分布在这里的1000多个物流网点、400多家物流企业,这些商品被装进卡车和货轮,运往世界各地。
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后,这些商品就会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最偏僻的乡村:上海某栋正在施工的摩天大楼塔尖上,可能会忽然响起“轰天雷”手机的巨大铃声;某个电力紧张的非洲村庄,或许正在享受来自华强北“超长待机”的馈赠。
那是深圳,乃至整个珠三角电子制造业野蛮生长的时期。2010年时,诺基亚和三星还在支配着全球手机市场。唯一能与之叫板的,就是那些千奇百怪,甚至有些荒诞的杂牌。人们只要进行一些简单的检索,就会惊奇地发现,一些产品来自一个名叫Huaqiang North的地方。
在华强北,没人说得清一款能开瓶盖的手机和一款保时捷跑车外形的手机,哪个会更赚钱。比产品差异化更重要的,是速度和产量——打造出“爆款”,在还没被模仿前大量铺货,及时收割市场。
效率至上的华强北,加速了产业链上游企业的扩张、整合。对市场嗅觉灵敏的南粤商人自然不会错过这块蛋糕:根据当时的深圳市工商局的统计数据,2006年,华强北聚集了300多家蓝牙生产企业,200多家天线生产企业,150多家电池制造企业,140多家主板研发企业,50多家外观设计公司和140多家组装企业。
在庞大市场的支撑下,哪怕是手机主板上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电感、电容,也有利润空间。即使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2008年,每天都有数十家企业进场华强北,产业总规模一度超过了1万家,这让珠三角成为全球手机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产业链最完整的区域。
华强北电子市场里一个不足半米长的柜台,可能就是某个厂家的“销售部”。在这里,一款手机从想法变成量产并不是件难事,从任何一个电子市场的楼上走到楼下,就能找到从设计到生产,从芯片到外壳的全部解决方案。
吴烨彬的“成功”也得益于这种精细的分工。在打造一款平板电脑时,他把主板方案外包给楼上的公司,自己只负责外观和结构设计。触摸屏、电池等非标准零件,只需要打几个电话谈好价钱,就可以快速定制。各个部分都在同步进行,吴烨彬只等样品到齐,然后组装、测试,最后把大宗物料送上流水线。
产品从研发到量产,只用了60天,并且供不应求。他甚至不敢回公司,总有经销商堵在门口,期望签下一份订单。
吴烨彬成名于此,直到今天,巨大成功带来的冲击仍然没有消退。在深圳南山区的一栋5A级写字楼里,吴烨彬回忆起这段往事,手指还会微微颤抖。
那是华强北最繁荣的时代,6000多家电子产品企业聚集在两个故宫大小的土地上,20多个市场密集相连,内部被分割成数不尽的小格子或柜台,就像蜂窝一般,肤色各异的淘金者每天都会挤满过道。赛格广场楼下端着15元一盒隆江猪脚饭的送货员,也在等待着一夜暴富的机会。人们并没有意识到,一个时代正在缓缓落幕。
当时,传统的手机公司一年只能推出1-2款新品,而在华强北,这是一个月就能做到的事。生存之道也在于此:依靠产业链带来的成本优势,打“机海战”,以量取胜。
“一年推出几十款手机,只要一款赚钱就够了。”深圳市手机行业协会秘书长余京蔚告诉记者,他在2007年来到深圳,当时还是一家手机厂商的采购经理。
协会那时还叫作“中国手机经销商联盟”,主要业务是为各省市来深圳找货的经销商组织“团购”。这些“省包”经销商赚钱后,很多都来深圳办厂。当时那场财富游戏里的玩家,只想跟上华强北的节奏,没功夫把成本浪费在研发上。仅剩的“研发”,就是在公板公模的基础上,加入一些“微创新”,正如当年在各大购物频道上广泛流传的“八星八钻,跑马灯”手机一样。
因为产品太过同质化,行业内的厮杀,只剩下“自杀式”的价格战。利润从最初的一台200元,降到最后的2元,勉强能够填补电费和工钱。
3G时代,电信运营商为了推广自己的网络制式,开始补贴手机厂商。华强北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品牌被排除在外,逐渐失去了市场。
另一方面,互联网电商的崛起,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。华强北的厂家还在为高昂的销售渠道成本发愁时,国产品牌的“千元智能机”已经在各大电商平台卖到脱销,这几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溃败来得和当年进场时一样迅猛,从2013年2月开始,每月“跑路”的手机厂商有200-500家。与巅峰时期的6000家相比,年底只剩下不到800家。
2015年,东莞兆信通信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家中拧开了煤气开关。这家年产量曾达到300万部的代工厂,因为资金链断裂,轰然倒塌。在绝笔信里,这位董事长写道:“愿赌服输,我输了。”
传音手机出现时,当时在做手机零件采购的余京蔚要经常“下厂”。他记得当时国内市场逐渐饱和,尤其是国产品牌手机崛起后,大量廉价手机成为“过剩产能”。
这成就了传音。20美元一部的超低价格、来自中国的双卡双待技术,再加上本土化运营——针对当地人肤色设计的拍照技术,这一套根植于华强北的组合拳,帮助传音迅速占领了非洲市场。
2
吴烨彬决定离开华强北。
他对突如其来的财富还没做好准备,银行卡里不断上升的数字反而让他焦虑,甚至恐惧:“我很害怕,一下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了,也不知道该怎么守好这一切。”
他把原因归结于自己的不自信。2004年,因为“对面就是香港”,吴烨彬在高考志愿栏填上了深圳大学,选了当时最热的工业自动化专业。
开学后,他发现这座城市与期待中一样繁华,身边同学也大多是家庭富裕的广东本地人。但对一个从小生活在江西大山里、每月生活费还要靠帮同学组装电脑来获取的贫困生来说,自己与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。
“那时觉得自己低人一等,班里的女生都不会正眼看我。”吴烨彬把身体窝进电脑椅里,陷入短暂的沉默。
这种自卑始终让他处在一种不安全感中,以至于他用“狮子在追一群羚羊,我只是跑出去的那一个”,来形容自己的成功。
他不断提到“向前奔跑”,甚至把自己比喻成西西弗斯,似乎只要停下脚步就会失败,会被抛弃,会重新被人看不起。
离开华强北,也是因为“不能在同样的高度做重复的事”。他拆开过ipad,从后盖开启的那一刻起,他就不断被震撼,惊叹眼前产品精妙的设计和构造。最后,他决定出去看看,“别人为什么能做那么好”。
华强北风云突变的那几年,吴烨彬先后在爱可视、英特尔做研发工作,逐渐远离了硝烟弥漫的市场。
这一时期,从华强北开始,整个电子制造行业都在经历剧烈的洗牌。
在手机产业的下游,华为、小米、OPPO、vivo等国产品牌统治了国内市场。那些曾经被小镇青年用来彰显个性的“八星八钻”手机,已经彻底沦为笑柄。如今他们再从裤兜里掏出手机,比拼的已经不是“炫酷”,而是牌子和档次。
产业链下游的剧变,也扯动着上游。大小手机厂商在华强北“百花齐放”,供应链上的企业也都有单可接。国产品牌崛起后,上游小厂被排除在供应商名单之外,失去了生存空间,运气好的被同行大厂收购兼并,运气差的只有关门跑路。
在这一轮整合中,很多深圳关外的工厂里,高速运转的机器并没有停止工作。同一条生产线上,小品牌的最后一批零件刚刚完工,大品牌的订单就迅速跟上。
余京蔚告诉记者,对那时的很多手机元器件生产商来说,“只要有量,就都是客户。”事实上,很多如今行业内的领跑者,曾有一段靠出货量生长的历史。
华强北某电子市场内部
如果把汇顶科技的发展过程绘制成一条曲线,人们会发现这家目前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指纹芯片公司,在2008年经历一个“历史性”拐点。
那时初代iPhone刚问世不久,触摸屏成为新的技术潮流。汇顶投入大量成本,研发出10点触控技术,但当时的大品牌手机厂商根本看不上这家小公司的方案。后来,汇顶成为中国电容式触控芯片第一大厂。如今,它为华为最新款的手机提供时髦的屏下光学指纹解锁功能。
同样在2008年,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,全球几家图像传感器芯片巨头为了止损,提高产品售价。一家名叫格科微的中国公司抓住机会,推出成本低于对手20%的产品,杀入市场。那一年,格科微在手机图像传感器市场的份额从国内第三变成第一,江湖地位从此确立。
除了指纹芯片和图像传感器,从提供基带芯片的展讯(现与锐迪科合并,更名为紫光展锐),到专注光学模组的舜宇光学,以至整个手机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,都曾在那个产业尚未完全成熟的时期,近乎跑马圈地般快速扩张。
如今深圳的科技公司,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做“底层取代”做起,最终发展为技术玩家。这是深圳很多“隐形冠军”的成长之路——人们的目光往往聚焦在华为这样的巨型公司,但除了华为,深圳还有成百上千家“汇顶”,他们站在各自领域的金字塔塔尖,成为深圳最关键的财富。
小米公司的多款红米系列产品都由国内最大的ODM公司(原始设计制造商)闻泰科技打造——从设计、采购物料到生产组装等全套服务均由闻泰提供,最后贴上红米的商标。
在一次采访中,闻泰副董事长肖学兵向媒体讲述:2006年,闻泰创始人张学政以10万元起家,开始做手机主板方案设计生意。当时为了“卖板子”,张学政扛着两台电脑,带着手机,在华强北挨个柜台推销,一遍遍把主板结构图演示给别人看。当时华强北的手机商嫌闻泰太小,最后“好不容易才说动两家用了闻泰的主板”。
这次华强北之行,成了张学政商业传奇的开端,也是闻泰科技鲜少提起的发迹史。
3
2014年,蛰伏4年的吴烨彬辞掉工作,带着他“就要挤出脑壳”的想法,回到熟悉的数码江湖。
这一次他要做的产品,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成品。
“如果在其他城市,一定有人说我疯了。”吴烨彬皱起眉头,“但在深圳,nothing is impossible。”
他要做一个可以随时装进口袋的“拇指电脑”,或者更直观地说,一根士力架大小的电脑主机。
“研发”是在一种非正式网络中进行的,吴烨彬只是把产品方案发给几个微信好友,很快就凑齐了团队。大家各有分工,有人负责设计电路板,有人提供外壳……
这是前一个时代的遗产——大家不是坐在井然有序的办公室,而是以项目为单位随机组合,一个好项目很快就能聚齐一群人或几家小公司。团队合作的基础,与兄弟情义无关,更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,一切都清晰而务实:大家都有钱赚。
“因为进入门槛很低,新产品不管听上去有多疯狂,都可以试验。自由的信息流把没有关系的厂商联系到一起,形成草根创新。”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创始人李大维说,他也是中国第一个“创客空间”上海“新车间”的创办者。
“拇指电脑”经过6个月的研发,第一批样机成功下线。机器完全实现了当初的设想:英特尔构架,能够流畅运行Windows系统。为了解决散热,在机器狭小的内部空间里,甚至还加入了两个拇指指甲盖大小的微型风扇。
产品构思之初,吴烨彬说自己从没想过要创造历史,或者重新定义什么。他只是在等车时看到一个摔倒在路边的姑娘,蹲在散架的笔记本电脑旁抽泣,这让他思考“电脑或许可以更方便一些”。
后来在媒体的报道里,他才得知,自己的新产品竟然是当时“世界上最小的PC”。
他给产品取了一个与“世界之最”完全无关的名字:光棍1号——它符合产品外形,更重要的,他说这是对自己当时感情状况的自嘲。
这一年,“大众创业,万众创新”,创客的时代到了。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咖啡馆外,创业者排着队想进去喝一杯。
那时吴烨彬的产品正在遭遇最关键的技术难题,他没有时间去喝创业咖啡,但并不妨碍他完成创客身份的转变。
产品上市前,他把几个关键的技术申请了专利。这曾是他需要绞尽脑汁才能绕开的雷区,现在他说,“可以分享,但不想被山寨”。
“光棍1号”成功了,但仅限于小众市场,成为一些硬件发烧友的玩具。吴烨彬清楚,相比4年前在华强北,如今的国内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已经完全不同,个人玩家越来越难打造出“爆款”。
“那些真正的大众消费品市场,已经被大公司分食。”吴烨彬说,虽然专注小众市场也能让自己衣食无忧,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此。
他无法让自己停下来,可国内市场已经没有了“向前奔跑”的空间。这一次,他把希望放在了广袤的远方——非洲。
“光棍1号”发布不久,吴烨彬遇到了自己的江西老乡、国内女鞋制造业大佬、华坚集团的董事长张华荣。
华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造了一个轻工业产业园,拥有8000名工人,与当地其他外资企业相比,规模更大,管理也更完善。
吴烨彬显然对女鞋一窍不通,但他需要一艘出海的大船。华坚专注轻工业多年,也想尝试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横向拓展。两个不同领域的人很快达成合作,他们都看到了,眼前是一片几乎空白的市场。
吴烨彬去了华坚集团的电子产业事业部,成为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航班上的常客。
2017年,吴烨彬与非洲当地青年合影
4
垦荒非洲的吴烨彬,并没有放弃国内已经成熟的生意。
那几年,创业的风口一个接着一个,每个人都想成为那只“飞起来的猪”。他身边突然多出不少创客,谈论着他们“可以改变世界的产品”,然后拿到风险投资。故事本来才刚开始,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圈子里的成功例子。
吴烨彬也在寻找机会,“光棍1号”已经更新到“光棍9号”,销量却一直不温不火。他最后还是决定做一款大众产品,接着把目光锁定在当时最热的“智能硬件”领域里最火的产品——智能水杯。
平时都用一次性纸杯喝水的吴烨彬,对杯子没有太多研究。这次为了做好产品,他选择了国内顶尖的骨瓷材料,芯片也用了“高大上”的英特尔。
以前做产品,一直都是买家找上门,这次他甚至花了血本,给新产品做了一次营销。在当时的一档热播综艺节目里,明星选手通关后,打开宝箱,配上金光闪闪的特效,里面就是这款智能水杯。
这款可以显示温度、定时提醒喝水,被他寄予厚望的智能水杯,最终的销量惨淡无光。后来他又尝试了智能鞋子、智能衣服,结果因为不熟悉供应链,统统失败。
“失败的产品能塞满一间仓库。”吴烨彬说这是他最不愿提起的伤心事,“当时的氛围实在太热,像我这样的老鸟也给创了进去。”
他重新回到属于自己的“创客”圈子,老实地做电子产品的应用创新。
那些想要飞上风口的“猪”,很多都掉到了地上。5年前开始的那一轮创新创业潮还在继续,但更趋理性。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喝了1000杯咖啡,终于拿到投资的硬件创客们,终究要走进真刀真枪的制造业战场。
在深圳,不管是什么来头的创客,在拥有1万人的工厂老板面前,天花乱坠或趾高气昂地宣讲自己“可以改变世界”的产品方案后,最终只会得到一个同样回应:“你要多少量?”
这个问题会让那些拿着10页PPT,或者两轮融资的创客认真思考,自己的产品是不是已经有明确的市场应用前景,以及要进入一个怎样的市场。
“很多创客对制造业知之甚少,甚至停留在1970年代,他们仅有的知识都基于一本《乔布斯传》。现代制造业如何构造生态系统和供应链,他们完全没有概念。”李大维在一篇文章里写道。他的工作就是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创客打交道,“苹果的设计师们每次来到深圳,富士康的人已经早早等在那里——天才设计师们想当然地认为,制造业就这么简单。”
全球最大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曾经有个明星项目——创下1000万美元预售纪录的Pebble智能手表。这块手表的设计者和工程师大多都是苹果公司出身,经验丰富。但当他们自己创业时,因为单量太少,富士康不接受他们的订单。最后,Pebble的发货时间比约定推迟了18个月,而且质量糟糕。
很多人只领会了乔布斯的创新精神,但太少人注意到,乔布斯并不是在车库里凭空想象出的苹果电脑。当时美国有上百家电脑公司,乔布斯和他们一样,都是为了研发出一种普通人也用得起的电脑——乔布斯的创新不仅因为他是个天才,也离不开市场的驱动。
5
在深圳南山区的办公室里,吴烨彬趿拉着一双大码拖鞋,他从老板椅上起身,后背上灰色的衬衫皱成一团。
他的办公室更像一个实验室,一张长桌占据了大部分空间,上面堆满电路板、拆开的笔记本电脑,以及各种电子设备的半成品。那个智能水杯也在桌子上,只不过已经变成了一个笔筒。
办公室的落地窗正对着大沙河高尔夫球场,在深圳,这是难得的景观。吴烨彬摆摆手,头也不回:“我没空看这些风景。”桌上的纸杯里是喝剩下的埃塞俄比亚咖啡。
深圳不乏新的故事:几个年轻人在深圳一家公司实习,其间问老板可不可以立项做机械臂,老板没有答应。实习结束后,他们拿到聘书,但一商量还是决定要做机械臂,于是放弃了offer。
他们没有先做好PPT去找融资,而是拿着实习工资在龙岗区租了民宅,再用两个月的时间做出样品,放到国外众筹网站上预售,筹到27万美元,成立了uArm公司,引起了很大关注。
李大维的团队曾去他们的住所采访,发现就是“四个小男生的宿舍”。一套三居室的房子,客厅成了他们的实验室,堆满了物料和半成品。两间卧室里放着两张高低床,几乎没有多余的家具。阳台上洗衣机旁边,是一台激光切割机。
“从这个宿舍就能看到创客的未来长什么样子。你有自信,你有热情,你就能有一条新的路,这条路长得像华强北。”李大维说,“深圳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创业者,宝安和龙岗满地工厂都是这样起来的,深圳的财富就是这样积累的。”
(本文由中国青年报独立出品,首发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及头条号,加入树木计划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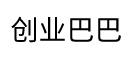




发表评论